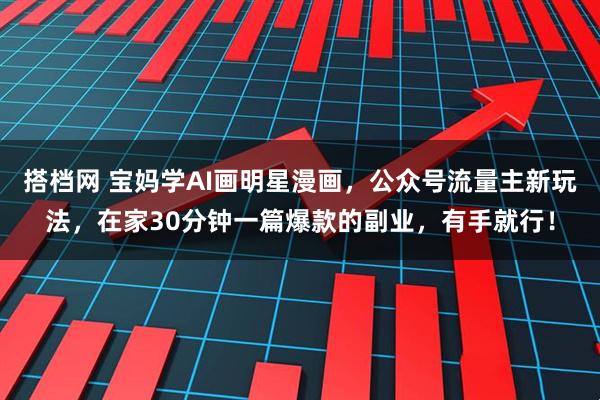【1951年初冬·北京】 “张校长,主席请您到中南海叙旧。”卫士推门而入。张干抬头,眼眶泛红,胸口却像塞进了石头——他曾把眼前这位共和国缔造者赶出校门,如今竟受其相邀。这一进门,尘封三十多年的旧账堆财网,会不会当场翻开?他心里没底。
火车从长沙驶向北平的两昼夜里,车厢摇晃得如同往事。张干靠窗,手里攥着一页又一页泛黄的信稿:一句致歉,一句感谢,改了又改,墨迹叠压得发乌。同行的老友周世钊劝他:“润之比你想象的宽阔,带着轻松的心吧。”张干苦笑,轻轻“嗯”了一声,像在应付,也像给自己壮胆。

时间拨回到1914年,湖南一师迎来这位年轻校长。张干三十出头,瘦削硬朗,眉梢总带一股“非礼勿言”的冷峻。他上任第一条规矩:课堂之外不准闹事,谁闹就记过。学生们窃窃私语,觉得新校长比刻板教科书还乏味。次年,省议会硬性摊派十元学杂费,贫寒子弟怨声四起。张干内心同样叫苦:上头卡死经费,他已卖掉自家古书典籍,才维持伙食供应,可学生并不买账。
于是那场声势浩大的“驱张”爆发。毛泽东执笔《驱张宣言》,四千余字针锋相对,句句见血。张干拿到宣言堆财网,脸色青紫:“开除闹事者!”话音一落,教师杨昌济、徐特立等人当面挡驾,表示若开除学生,教师集体罢课。张干被迫让步,只给毛泽东记大过。但浪潮难止,数百名学生冲进办公楼,高喊“张干下台”。一个月后,他卷起铺盖走出校园。
外界把他骂作“反动爪牙”。只有少数人才知,他之前连夜跑省都督府要拨款,被拒绝后回校仍要装出“不为所动”的脸色。张干不善言辞,不懂妥协,最终成了众矢之的。也正是那段时间,他第一次深刻认识到什么叫“民意不可违”。

抗战胜利后,张干已在乡间教书。1945年8月,他读到重庆和谈消息,心急如焚,连夜起草电报劝毛泽东赴渝。“幸勿固执”四字写得直白,旁人劝删,他坚持——还是那股倔劲。电报发出后,他越想越不安:会不会又把学生得罪?字句里的上下尊卑,他早年讲究的“礼”此刻像钉子扎心。
1949年后堆财网,新中国百废待兴,张干却日子清苦。家里十几口,靠他微薄薪水度日。有人提议向毛主席求援,他摆手:“旧账未清,哪能开口?”这种执拗,使他在物质上捉襟见肘,却让晚辈既心疼又钦佩。
1950年国庆前夕,周世钊到长沙探望。临别前一句“润之让我带话”让张干沉默。那晚他辗转反侧到天亮,最终只托周一句“望主席保重身体”。第二年接到北上请柬,他不再推辞。火车抵京,冬风削面,他挺直腰杆,像三十多年前立在讲台。
毛泽东迎上来,先敬了一个军礼:“张校长!”声音洪亮。张干鼻子一酸,忙回一句:“润之。”两个人相视而笑,却都红了眼眶。几杯热茶下肚,彼此揭开疙瘩。张干低声道:“我那时太刚,误解了你们。”毛泽东摆手:“我当年也虎,不懂校长苦心,多读半年书是好事。”

席间毛泽东叫来孩子:“这是我的老师,你们要记住。”这种朴素的尊师之念,让张干心里暖得发烫。临别,主席让人送来鹿茸精和一笔稿费,说是“补偿老师营养”。张干一推再推,最后收下,叹道:“谁能料到,昔日记过的学生,如今给我送药。”
1963年春,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奉命带着两千元新币上门。张干连连摆手:“我已接受太多。”张平化笑:“主席吩咐,不收就是不给他面子。”倔老头只好将钱塞进抽屉,回身又拿出几册旧书,硬塞给来客:“替我带给主席,他爱这一口。”
1967年元旦后,张干病体日渐沉重。1月2日清晨,他唤儿子到床前,断断续续吩咐:“替我……给毛主席写封信……谢他的照顾……说我没能再见他,是遗憾。”话落,气息微弱。手背上的青筋慢慢松开。儿子握着那双枯瘦的手,点头哽咽:“爹,孩儿记下了。”

信写好后,贴着红色“急”字的信封很快抵达中南海。卫生员说主席读完沉默良久,只嘱咐:“替我向张校长家人致意,安排好后事。”没有更多话,却意味深长。世事倥偬,师生情却在那一刻定格。
张干走时八十三岁,一生清寒,却留下厚重的教育情怀与骨气。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谈话中说:“当年张干不肯破例,他是为护学校。我现在理解他,也感激他。”短短一句,给了老校长最朴素的评价。二人从碰撞到体谅,相隔半个世纪,许多观念潮涨潮落,最终沉淀为相互尊重——历史的锋芒或可割裂时空,但真诚总能跨越裂痕,再度相握。
金御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